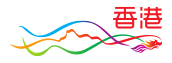前任财政司司长网志
喇沙与我
上周末,我和家人出席了母校喇沙书院的旧生会周年聚会,跟三位带领喇沙多年的修士和众师兄弟聚首,一起话当年,唱校歌,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。
我在1985年开始在母校喇沙书院教剑,到今年刚好三十年。三十年来,剑队的工作除了让我可以维持运动习惯,也是我在工作以外,最重要的心灵寄托之一。
 |
| 周年晚会当晚,喇沙剑击队难得「N代同堂」,我第一代的学生,如今都已经是四十开外的爸爸了。 |
移民美国之前,我家住在西洋菜北街,每天早上上学、下课回家都是走路;回流香港之后,我仍然是喇沙「街坊」,住在界限街附近。我十分感激彭亨利修士和朱永斌修士。彭修士担任喇沙小学校长长达27年,是我的小学校长,后来也让我儿子到喇沙小学插班,朱修士则是中学部校长,是他批准我在周末负责训练剑队。自此之后,旧生、家长和教练的三重身份,让我和母校维持非常密切的关系。
当我还在大学念书时,已经有参与教练工作,当过几年助教,当年我甚至考虑过转做全职。这个想法最后虽然没有实现,但命运却带领我回到母校教剑。喇沙剑队的一套训练方式,还是我当年在麻省理工剑队使用的一套,这套方法让MIT剑队有不错的成绩,成员之一Johan Harmenberg后来还拿了奥运金牌和世界冠军。我有机会将这套方法带回香港传授给年轻一辈,总算没有白费当年的一番苦功。
 |
| 这张相片拍摄于80年代,图中的三位剑手,都有出席上周的聚会,你能把他们认出来吗? |
八十年代,剑击在香港中学界颇为冷门,喇沙的剑手都是在体院前身银禧体育中心受训,或由高年级学生负责指导,直至我接手,剑队训练转为校内为主。由于学界对手不多,我们很快就打出了成绩,主要对手是基智中学和后来进步神速的男拔萃,后者后来更成为了我们多年的强敌。
认识香港学界运动比赛,都知道学校之间竞争非常激烈,喇沙和男拔萃之间的竞争,更成为两间学校传统的一部份。从成人的角度,或许会觉得年轻人「乜都争餐死」是幼稚无聊,但我作为过来人,却深信这些竞争,是教育中非常重要的部份。通过运动、音乐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良性竞争,年轻人可以不断挑战自我,发掘潜能,体会何谓体育精神;而他们在过程中学习合作、奉献,在个人和团队层面建立身份认同,和队友之间建立一生不渝的真摰友谊,相较于奖牌和奖状,这些东西对个人产生的影响就更为深远。
 |
| 喇沙曾经赢过11次学界剑击总冠军,在2011年更曾赢得第一次「大满贯」。 |
喇沙剑队出产过不少香港青年军,获选入港队的也有几位。他们后来虽然没有以剑击为志业,但大都转做了教练。部份人留在喇沙担任我的拍档,也有人些在剑击学校授课。今时今日喇沙剑队的教练团包括了八十年代的第一代剑手,和2000年后毕业的新秀,大家每个周末会一起习训,学界比赛进行期间,出席的教练人数,有时比参赛剑手还要多,在比赛场内颇为突出。喇沙之内,同类的「傻佬」遍布田径队、泳队、足球队等校队,这些旧生教练愿意在毕业后不收分文贡献母校,背后的推动力就是一个字: brotherhood。
每当我置身旧生圈子,无论是叫口号或者唱校歌,都令我觉得喇沙仔对学校那股近乎狂热的归属感,和近年流行的所谓「本土」意识有着不少共通之处,两者都是对本身的身份、传统和文化,有着强烈的感情和自豪感,这种情感,大至国家民族,小至一间学校,都会存在,亦不只限于所谓传统名校。在喇沙圈子之中,这种感情和自豪感会转化为一种正面的动力,推动每一代的喇吵仔愿意为母校作出无私贡献。我相信这一种感情和自豪感,同时存在于所有香港人之中,我们对香港深厚的情感,同样可以团结成一股正面、具建设性的力量,推动香港变得更好,让香港整体都能够得益,而绝对不止于一种封闭式的、消极的、甚至是具破坏性的保护主义。
2015年12月27日